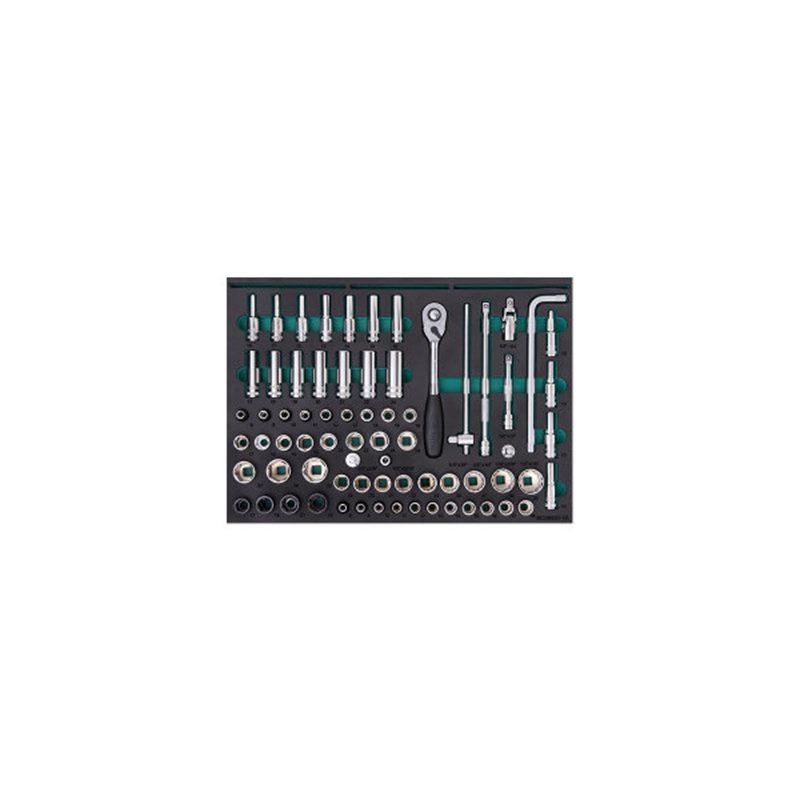相同的歌,再写一百首也没有成就感
乐队成员:鼓手武锐、贝斯郇峰、吉他李伟、主唱马玉龙、键盘刘光蕊(从左至右)。
声音碎片乐队在巡演后台花样“练功”。
声音碎片乐队在巡演后台花样“练功”。
声音碎片乐队在巡演后台花样“练功”。
声音碎片乐队在巡演后台花样“练功”。
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堪称是2022年度极具重量的华语专辑,不耍花招,不使手段,不说虚妄语,不使文艺腔,真刀真枪,硬桥硬马。但对于声音碎片乐队来说,这又是一张自我革新的专辑,刻意求新求变,对老歌迷不够“礼貌”,年轻人要听懂还要有足够的经历和阅历,身兼主唱和主创的马玉龙接受南都采访时说,不想再做青春期的表达,尽量真实的表达当下的所思所想。
声音碎片成军超过二十年,是最重要的中国摇滚乐队之一,乐队成员包括主唱马玉龙、吉他李伟、键盘刘光蕊、贝斯郇峰、鼓手武锐,2019年的专辑《没有鸟鸣,关上窗吧》曾拿下第二十届南方音乐盛典“最佳摇滚艺人”,代表作《优美的低于生活》一句“相爱吧,终有一散的人们”被文艺青年广为传颂,《情歌而已》《黄金时代》等都是广为传唱的名曲。
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发布之后虽然有些争议,但在9月24日的声音共和Livehouse,乐队巡演广州站的现场还是挤满了人,到场还多是年轻人,《致我迷茫的兄弟》《送流水》等歌曲还是大合唱,唱到新歌《愿你旅途漫长》时过千人的场地又安静地让人动容,歌迷是听到了心里。
20年后的这第五张专辑,马玉龙写歌的心态和态度都变了,不变的当然是声音碎片本身的气质,以及一个摇滚乐队的诗性和担当。以下为马玉龙的自述。
01 求新求变
可以肯定的是,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是一张刻意求新求变的专辑,跟原来的声音碎片区别很大,这算是一种追求吧,对老歌迷肯定是不礼貌,因为不再是习惯的路子,但对于乐队、对于创作来说,只习惯于一种风格会没有成就感。
如果再让我写任何一首之前风格的歌,几分钟就可以完成,因为那种路数已经很熟悉了,但是可以求新求变,其实是更难的。新歌上线之后被老歌迷批评,包括歌词都被批评。我是深思熟虑过的,这些歌词看上去像大白话,其实只是另一种新的写法,原来那种文艺腔对我来说轻车熟路,但人年纪大了,不能再用那种表达方式。
为什么刻意求新求变,先举个披头士的例子,在《Sgt. Pepper’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》这张伟大的专辑之前,他们和我们的“小虎队”差不多,唱的是情情爱爱的内容,四个人看起来青春靓丽,不仅在英国,在全世界都受欢迎。但他们刻意求新求变,成为最伟大的乐队。
鲍勃·迪伦也是,唱民谣的时候已经是超级巨星,但他突然有一天唱起了摇滚,很多人不适应,追着骂他。但对于写作的人来说,总是重复原来的写法没有了快感,也没有了成就感。我举这两个经典的例子,他们成功了,当然也有失败的,但必须要写点做点不一样的,成不成功需要时间。
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上线之后,有很多不好的评价,我看到一句“套用一句某英国乐评杂志评论平克·弗洛伊德《藩篱之钟》的话,这张专辑散发着令人不舒适的中年感”,说实话还是有点伤心,当然平克·弗洛伊德前几张专辑都足够伟大,但我不喜欢这句“令人不舒适的中年感”,虽然可能是中肯的,但流行歌总是唱“青春”、“远方”、“理想”这些东西,市面上差不多99%是这样的表达,像声音碎片出一张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,唱的不是常见的这些内容,就有人不适应了。
声音碎片以前也是青春期表达,上一张专辑《没有鸟鸣,关上窗吧》稍微突破一点,总体还是青春期表达,但是到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就肯定不是,一点都没有,这就是刻意的结果。我完全可以继续用青春期表达,手到擒来,但是没有成就感,乐队一起大家排练的时候也觉得没意思,就像做行活,流水线一样,再写一百首也没有成就感。
当然青春期表达没有任何问题,刘德华就可以,一辈子唱青春期唱情歌都可以,没有不好。但我们到了这个年纪,就是另外一种表达,尽量真实地面对,尽量真实地思考,尽量真实地表达所思所想,当然只是尽量,完全真实是做不到的,任何写作都做不到,回忆录也没有完全真实,日记都有假的。
真实的表达不是近似生理上的排泄,写作和写歌都需要技巧。就像这些年,有很多问题想不通,但必须得写点东西,表达可以不充分,别人可以不同意,但作为写歌的人,必须写点什么。
如果只是写中年人的世界,这张专辑还要再沉淀几年,但现在箭在弦上不发不行了,必须发声。其实我写歌的时候头脑特别清楚,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想得清清楚楚,不能总是活在青春期的梦里,理想不陪你玩儿,你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,必须有自己的想法,自己的态度,才不至于被裹挟。
02 无我无穷
专辑的名字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就是字面的意思,一个人的肉体是有限的,但你的想象、精神世界可以是无穷的;肉体可以被限制,但精神不应该被束缚。
我在专辑中虚构了一些人,比如“康小午”、“方可”,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态度,有中年人的孤独,但这些人不是我马玉龙,是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虚构的,这样可以有更好的表达。在这张专辑里,“我”字出现得极少,几乎没有,刻意避开“我”。说实在的你那点儿事儿根本不重要,身为一个写歌的人,不要总是“我、我、我”。
年轻的时候都是“我”,“我要去远方”或者我要干这干那,但现在超过四十岁了,上有老下有小,“我”完全不重要,很多人都不做乐队了,挣点钱就得了,我们还能写点东西,也就这样了。
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里“我”只出现了一次,就是最后一首《是你》,“当我孤身远行”,因为是一首情歌,必须出现“我”,其他就是刻意没有“我”,其实有没有“我”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说话,要出声,觉得我说得唱得不行你可以来,大家一起发声,声音才可能大。
《电子荒野》有提到“真人秀”,在这里不是特指某个综艺节目,而是特指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摄影机之下,没有人可以例外。具体的某个真人秀节目,你可以喜欢,可以不喜欢,你是有选择的。
很喜欢一位希腊诗人卡瓦菲斯,他有一首诗《伊萨卡岛》,其中有一句“但愿你的旅途漫长,充满冒险,充满发现”,我借用了这句诗,写成了《愿你旅途漫长》,这首歌在专辑中算是比较早期的,在作曲上还有参考意大利电影配乐大使莫里康内,一个班卓琴加一个口琴,那种苍凉空旷的意境,在专辑中也是一种情绪。
文案中多次提到的“尴尬”,其实不管有意无意,很多艺术品都是金钱在推,聪明人似乎应该顺着走,跟着嘻嘻哈哈,但偏有人板着面孔说些不招人待见的话,就很尴尬。但不能所有人都被娱乐化推着嘻嘻哈哈走,我要保持一点局外人的角色。
我原本是特别笃定的人,特别清楚自己要干什么,但这几年让我有了动摇和怀疑,反思之前笃定的东西都是对的吗。我自己也不认为这张《有限身 无穷念》有多好,很多只是有感而发,当下的环境,这种反思和自我怀疑是重要的,也是应该的。在中国做乐队,做够二十年,并不容易,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想法,很多混几年就解散了。
03 奇花异草
我一直觉得摇滚乐最伟大的东西,不是英伦摇滚或者美国朋克,约翰·列侬拿一把箱琴唱《给和平一个机会》,就是摇滚,而不是长发、纹身、耳钉。我认为摇滚乐的内核就是自由、不从众、不媚众,而且不取悦于人,像鲍勃·迪伦会和自己的歌迷对着干,按照市场规则商业需要是不可以的,但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,我想怎样写就怎样写,这才是真正的摇滚。
我一直喜欢的摇滚乐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朋克起来以前,鲍勃·迪伦和约翰·列侬也有自己的小世界,但他们的表达和当时的时代是合拍的,而不是像后来的朋克、后朋克,来来回回都是自己那点烂事儿和个人情绪。
鲍勃·迪伦和约翰·列侬之所以伟大,还在于他们太复杂了,不是只有一面,约翰·列侬也有情歌,也有写给儿子的歌,他是很复杂的,简单成不了约翰·列侬。不能头脑简单,表达必须多元化,但首先一点,你得关注你生活的这个时代,那是你的生活,你得诚实地面对它。
科特·柯本这些人,活了27岁,其实挺亏的,长得又好,演奏简单,有那股劲儿,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觉得他们是英雄,现在觉得他们还是小孩,早早离开,失去了别的可能,没有了别的可能性。
电台司令(Radiohead)是把我从科特·柯本和Grunge拉出来的,他们的器乐、演奏、表达都更复杂,让我从所谓的民谣歌手的身份摆脱出来,虽然他们也有民谣的根,电台司令是全世界唯一一支所有玩过的音乐我都了解的乐队,包括汤姆·约克和强尼·格林伍德的很多个人项目,我全部都听过,年轻的时候还喜欢和他们比一比。
这么多年跌跌撞撞,我觉得真正好的生活态度,就是做奇花异草。最漂亮的玫瑰花,那是迈克尔·杰克逊,但不可能所有人都是他,不可能所有人都是玫瑰花,必须是各种奇花异草,才有生态。
能够坚持这么多年做乐队,就是在花园里做奇花异草,不是娱乐机器中的螺丝钉,而是一棵特别的花草,独有的一份儿,不好看,但缺了这一棵,整个生态就不完整。
我们就是那几棵奇花异草,像我们这样的奇花异草多了,花园才美好,如果方圆几里全是汪峰,那就不正常,当然汪峰老师有他存在的意义。
就像声音碎片这样的乐队,也有面对所谓主流的时候,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摆在面前,你要不要,考虑到现实处境是“要”,但不能所有人都被钱推着走,那就太糟糕了。
采写:南都记者 丁慧峰 实习生 姜文君